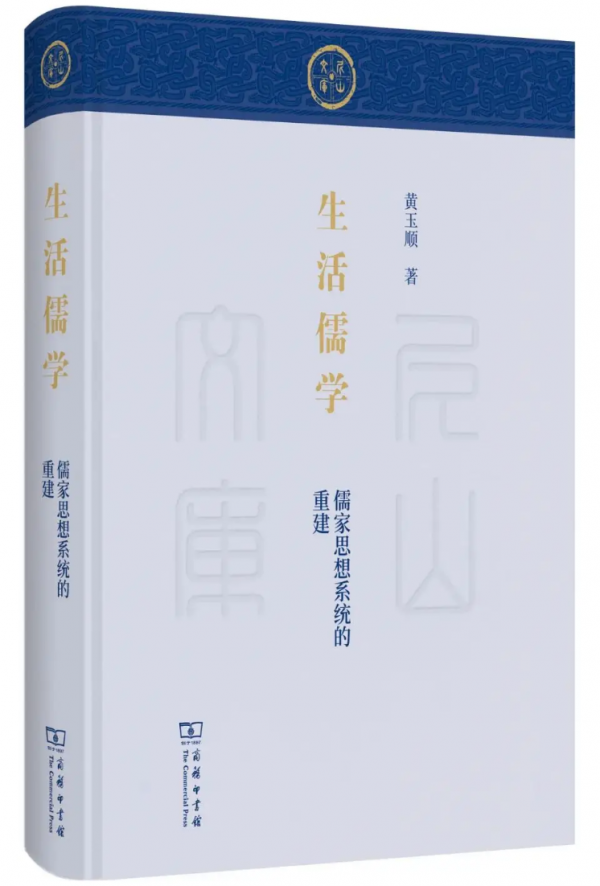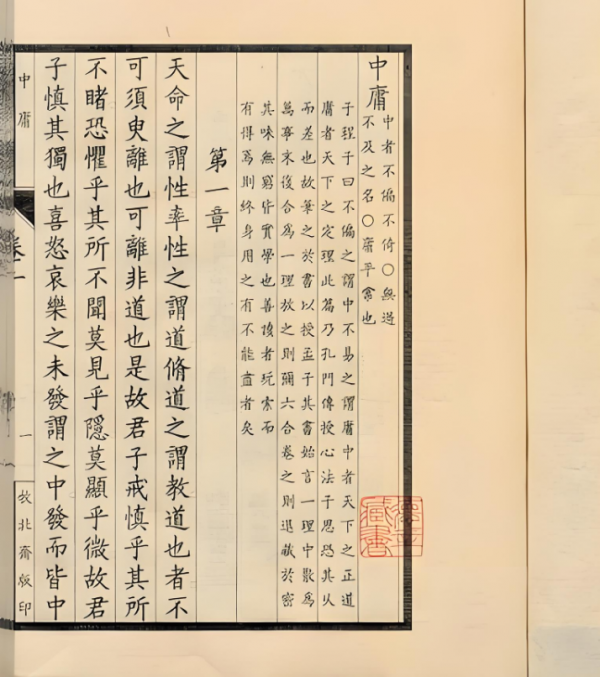摘要:针对当代西方政治学家对儒家政治哲学的三点主要质疑,作为当代儒学重要流派的“生活儒学”的政治哲学申明三点要义:一是构建作为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理论背景的“生活儒学”思想体系,以此为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奠定基础;二是构建生活儒学的次级理论——“中国正义论”,即情感伦理学的儒家表述“仁爱正义论”,以期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形态——“国族自由主义”;三是揭示儒家的自由传统,进而阐明儒家的“自由保守主义”本质。
关键词:生活儒学;政治哲学;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正义论
当代西方政治学家对儒家政治哲学提出了三点主要质疑。其一,作为一种古代意识形态,儒家政治哲学如何能与现代价值相协调?其二,当代儒家政治哲学既然吸纳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自由”价值,那么,它究竟具有哪些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儒学特征?换言之,这种政治哲学何以还是“儒家”的?其三,上述既超越古代儒学又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应如何定位,是“自由主义”的一种,还是某种“保守主义”?针对这些质疑,笔者已在不同场合做出过一些回应,本文是对这些回应的集中阐述。
何以“当代”:儒学与自由主义问题
质疑之一:作为一种古代意识形态,儒家政治哲学如何能与现代价值协调?对于这种质疑,笔者建构了“生活儒学”(life confucianism)思想体系,将其作为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背景,为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奠基。
黄玉顺:《生活儒学——儒家思想系统的重建》,商务印书馆
(一)抽绎儒学基本原理:生活儒学概要
提及“儒学”,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古代儒学”。但事实上,“现代儒学”已经是既有的“历史事实”。不仅如此,生活儒学实质上是“当代儒学”而非“现代儒学”。这里涉及“当代”与“现代”的概念区分,“这需要理解‘当下性’(immediateness)这个概念。这里的‘当下’,并不是指流俗时间概念中的、与‘过去’和‘未来’相对的‘现在’,而是一个‘前时间性’的概念,意味着‘前主体性’‘前存在者’的存在,这也就是生活儒学所讲的‘生活’”。这是因为“当代性所意谓的事情,乃是非时间性、前时间性的当下”,因此,“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既不同于现代性(modernity),也不同于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
1.儒学的“历史形态”
迄今为止,儒学已有三种历史形态:一是作为“周孔之道”“孔孟之道”的王权封建时代的原典儒学;二是“汉唐经学”“宋明理学”那样的皇权专制时代的帝制儒学;三是现代儒学,尤其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和21世纪以来的当代新儒学。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儒学的上述不同历史形态都是“儒学”。这就表明:在这些“儒学历史形态”背后,有一套一以贯之的“儒学原理”。这套原理可以超越历史时空,演绎出面对现代生活的现代儒学形态,即儒学能够与现代价值协调。今天研究儒学,首要的事情就是严格区分复数的“儒学形态”与单数的“儒学原理”。
2.生活儒学的原理
揭示上述“儒学原理”,正是生活儒学的主旨,以便由此开显出现代儒学,包括现代儒家政治哲学。这套儒学原理旨在“解构”儒学各种历史形态中的形而下学(如“三纲”那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形而上学(如“理学”“心学”),因为它们都是“存在者化”的思维。这就意味着追溯“前存在者”的“存在”(Being),亦即“生活”的存在观念及其所蕴含的“仁爱”情感观念,从而导出“现代性的存在者”建构,由此重建儒家的形而上学、形而下学,包括建构儒家现代政治哲学。
3.儒家的“正义”理论
上述生活儒学原理在伦理学及政治哲学层面的体现,就是建构隶属生活儒学的次级理论“中国正义论”(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即儒家正义论,或曰儒家“制度伦理学”。这种正义论的核心观念架构就是“仁→义→礼”的理论结构。
“礼”泛指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一方面,“礼”是普遍而永恒的,因为任何群体生活均需一套制度规范,每个成员均需遵守这种规范,此即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不学礼,无以立”;但另一方面,“礼”是特殊而暂时的,因为历史上任何一套具体的制度规范都不可能永远正义,都必然面临解构与重建,此即孔子所说的礼有损益。现代社会的规范及其制度,就是“礼”的现代性形态。此前,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王权封建时代的制度规范和皇权专制时代的制度规范。
“义”指正义原则,这是上述制度规范,即“礼”赖以建立、为“礼”奠基的价值原则。儒家正义论有两条正义原则:一是正当性原则,它要求制度规范的建构出自一视同仁的“博爱”情感的动机,此即孟子所说的“义,人之正路也”;二是适宜性原则,它要求制度规范的建构具有适应特定历史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效果,此即《中庸》所说的“义者,宜也”。
“仁”即仁爱的情感,这是上述“正当性原则”的实质性内涵。这种仁爱精神要求在制度规范的建构中克服私域的“差等之爱”的“偏爱”,发挥公域的“一体之仁”的“博爱”,并依据上述“适宜性原则”的要求,将这种“博爱”落实到合乎时宜的制度规范的建构中。此即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即“仁→义→礼”的观念结构。
(二)吸纳现代政治价值:以“自由”价值为核心
根据上述“仁→义→礼”的儒家正义论原理,面对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儒家显然要求建构现代性的制度规范,即从儒学原理中“开出”现代价值。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所说的“内圣开出新外王”,便是这样的价值诉求。在这些现代价值中,最核心的无疑是“自由”价值。如我们可以看到严复、徐复观、张君劢等人的“儒家自由主义”,乃至郭萍新近提出的“自由儒学”等。
1.关于“国民政治儒学”
根据儒家正义论原理,特别是适宜性原则,顺应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现代政治生活,生活儒学提出了“国民政治儒学”。笔者曾谈道:
我们所谓“国民政治”(civic politics),其实也就是现代性的政治;这种政治渊源于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以作为现代社会主体的国民为政治主体。如果套用林肯《葛底斯堡演讲》(The Gettysburg Address)“民有、民治、民享”的说法,那么,“国民政治”不是说的林肯所谓“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而是说的“the politics of the citizens, by the citizens and for the citizens”,即是“国民所有,国民所治,国民所享”。
国民政治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人权观念。“人权”(human rights)概念实质上指个人的权利,即是个体主义的观念,所以也表达为“personal right”;这个概念的首要的、核心的观念就是个人的“自由”,其关键是划分“群己权界”,特别是“权力”(power)与“权利”(right)之间的分界。
显然,生活儒学的“国民政治儒学”吸纳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个人自由。个体名词“citizen”和集体名词“people”的严格区分,其实是当今政治哲学界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两者有实质差异,“people”往往被利用为“人民的名义”。这与笔者的儒家自由观是密切相关的。
2.关于“自由主义儒家”
鉴于上述缘由,笔者曾做过一个讲座,主题为“自由主义儒家何以可能”,其中谈到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给我贴上“自由主义儒家”的标签。说我是“自由主义儒家”,是因为从2013年开始,我进一步演绎,把“中国正义论”这个适用于古今中外的建构,应用于当下的中国,也就是正在发生现代性转型的中国,讨论其制度建构问题,这个时候才涉及了所谓的“自由主义”问题。所以,如果仅仅在儒学的制度伦理学层面,且是面对现代性问题的时候,你叫我“自由主义儒家”,我是承认的,但也仅此而已。但下文将会说明:生活儒学的政治哲学,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毋宁说是“保守主义”的。
这里有一点应当注意:上述讲座并没有区分“自由主义儒家”和“儒家自由主义”。但严格来说,这两个概念本质上是有区别的。安靖如(Stephen C. Angle)教授就指出:“在我看来,‘儒家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儒家’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前者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形式,与儒学共有一些特征;后者是儒学的一种形式,其中自由的作用受到特别强调。”
安靖如教授进而判定:生活儒学的政治哲学作为“自由主义儒家”是“儒学的一种形式”。他在谈到生活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区别时指出:“我怎么理解生活儒学跟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我的答案是,我觉得它们应该是两回事。自由主义有它自己的传统……而生活儒学明明是另外一种传统,就是儒家传统的一个发展思路。”我当时回应:“我用的是‘自由’,而不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确实是产生于西方的东西;而且,对于我的生活儒学来说,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而仅仅是其中的形而下的、政治哲学层面上的立场,就是说,我是主张‘自由’这个现代价值的。”
毫无疑问,生活儒学的政治哲学确实吸纳了自由主义的“自由”价值,尽管这种吸纳并非照单全收。
何以“儒家”:儒学、情感伦理学与国族自由主义问题
质疑之二:当代儒家政治哲学既然吸纳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自由”价值,那么,它有什么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儒学特征?换句话说,这种政治哲学何以还是“儒家”的?
这是不少学者对当代儒学(包括对生活儒学的政治哲学)提出的质疑。例如,方旭东教授曾谈道:“你用中文的词‘礼’,英语可能是用另外一个词‘institution’(制度),但是,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实质上还是西方的概念。不仅如此,事实上,连‘民主’‘自由’这样的词语,你也不回避。这就是说,在基本的工具——语言上面,你使用的也不完全是带有中国性的词语。即便你全部换成汉语的词语,这个问题依然存在,人家可以这样说:你讲了半天,其实就是西方的这些现代基本价值,哪个地方是儒学的?”
对于这类质疑,生活儒学做出了若干澄清。早在21世纪初,笔者即已指出了移植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中国自由主义有“两大脱离”:既脱离中国现实,也脱离中国传统。此后,笔者主要建构了生活儒学的次级理论“中国正义论”,即情感伦理学的儒家版本“仁爱正义论”,认为这样的当代儒家政治哲学可以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形态“国族自由主义”(national liberalism)。
笔者十分同意安靖如教授的这种态度:“在政治哲学领域中,本书主张儒学与自由主义传统之间一定程度的汇聚(convergence),但也主张维持儒学与现存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制度之间的区分。”表面看来,生活儒学似乎确实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价值,事实上,其自由观念与西方自由主义之间存在着若干重大根本差异。这里,笔者主要谈两点差异,即安靖如教授所说的“价值观”和“制度”两个层面的差异。
(一)伦理学差异:情感伦理学的儒家版本
关于“价值观”层面的差异,这里主要谈谈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的伦理学问题。对方旭东教授的上述质疑,笔者当时作了三点回应,其中之一就是:儒家的真正的独特性在于用唯一的一个观念来说明一切事物,说明宇宙世界中的一切存在者是何以可能的,这个观念就是“仁”或“仁爱”。儒家用仁爱来解释一切,没有比仁爱更本源的事情了。所以,笔者的判断非常简单:如果你试图建构一个理论系统,用以说明宇宙万物,那么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只要你不是用仁爱来给出一切、阐明一切,那就不是儒家;反之,哪怕你是个美国人,只要你用仁爱来给出一切、阐明一切,你就是儒家。
这就恰如蒙培元先生所指出的,“情感是全部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成部分,甚至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儒家哲学就是情感哲学”;“儒家的情感哲学如果能够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仁’”。
为此,笔者特别强调了“情感伦理学的儒家版本”——“仁爱伦理学”(Benevolent Ethics)。众所周知,西方伦理学包括康德及罗尔斯的伦理学,其主流是理性主义的,比较排斥情感;与此同时,西方也存在着苏格兰启蒙学派的那种情感主义伦理学。但是,与这种“情感伦理学的西方版本”不同,“情感伦理学的儒家版本”是“仁爱伦理学”。因此,在儒家看来,一切正义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仁爱”情感问题:“差等之爱”的偏爱情感导致利益冲突;而“一体之仁”的博爱情感则可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这就表明,儒家正义论是“仁爱正义论”。
这里的“仁爱正义论”不仅是一种“正义论”,而且是一种“伦理学”。因为生活儒学的正义论并非罗尔斯正义论那样的针对现代性的特殊正义论,而是一种作为“基础伦理学”(foundational ethics)的一般正义论。
(二)制度性差异:超国族的自由主义
关于“制度”层面的差异,这是一个有待深入研讨的重大的时代课题。西方自由主义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启蒙时代的自由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第三个阶段,现在学界也把它译为“新自由主义”。在英文里有两个“新”,一个是“new”,一个是“neo”。笔者现在写文章时,把“neo-liberalism”译为“新古典自由主义”,以示区别,因为这两个阶段的自由主义的立场是截然不同的。新自由主义认为,第一阶段的古典自由主义过于自由放任,会造成一些问题,于是他们想加以矫正,强调政府干预,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这恰恰可能违背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因为自由主义在政治概念上的“自由”,就是“right”和“power”之间的界限,也就是公民个人的权利和政府、国家的公共权力之间的界限。
但是无论如何,这里有一点必须意识到:迄今为止,西方自由主义乃国族时代的产物,即“国族自由主义”(national liberalism)。“国族”(nation/nation-state)或译“民族国家”,只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以来的世界格局。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西方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人自由”在政治制度(包括民主制度)上的落实,其“个人”其实就是某个国族的“国民”,其“自由”其实只是“国民”的自由。于是不难发现,这种“自由”的权利是一种“国民待遇”。换言之,不属于这个国家的个人并不享有这种权利待遇。例如,不能享受这个国家的福利待遇。这就是我们经常能看到的“双标”现象,它表现在现代国家的制度建构的方方面面。且以“迁徙自由”为例,这种自由的限制就是“国界”;即便给予“免签”的待遇,也只是一种“给予”的临时权利,是一种“不自由”的表现。
当然,不可否认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出现了一些超越国族的议论,但这些零星的议论并不能在整体上改变“国族自由主义”的性质,反倒证明了笔者所说的“超越国族视域”趋向的出现。同时需要注意:那些关于“国际正义”的议论,其前提仍然是“国”,即并未超越国族视域。
这意味着:自由主义的未来发展需要超越国族视域,即诉求“超国族的自由主义”(super-national liberalism)。当然,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思考“超国族时代”(super-national times)即如何“超越现代”的问题。实际上,“欧盟”就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现象。但要注意:这并不等于那种时髦的所谓“现代性反思”或“启蒙反思”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曾指出:汉语“世界主义”有四种含义,古代的两种“世界主义”或两种“天下主义”,即王国天下主义与帝国天下主义(古代帝国主义);当代的两种“世界主义”,即国族性世界主义(现代帝国主义)与超国族世界主义,后者可谓“大同主义”。
王国天下主义是封建的世界主义,它是由一个王国与若干诸侯国组成的世界体系,例如西周时期的情况。这种天下主义是由王国的王族掌控天下秩序,其政治理念就是所谓的“王道”。这种天下主义是由帝国的皇族掌控天下秩序。显然,笔者所思考的“超国族的自由主义”属于“大同主义”(datongism),即“超国族世界主义”(super-national cosmopolitism)。所谓“超国族世界主义”实质上就是“超国主义”(supranationalism)(或译“世界主义”),不再以国族为基础,而是国家消亡之后的情景。显然,这在目前基本上还只是一种理念性的存在,但这种历史趋势已经出现了若干征兆。
在这个问题上,儒家的思想资源可以有所贡献,但这绝非目前时髦的所谓“天下主义”的“天下体系”。而“大同主义”则确实蕴含着儒家的思想资源。“大同”一语出自儒家典籍《礼记·礼运》: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是谓小康。
笔者曾提醒:“《礼记》所设想的‘大同’是国家产生之前的情况,尽管它实质上是一种社会理想;而我们这里讨论的‘大同’则是指向未来社会的,今天也往往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大同’一词的。”
这很容易令人想起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大同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去国界”主张。首先他认为“大同”社会必须“破除九界”,他列举了种种“有国之害”并提出“去国界”,然后指出“欲去国害必自弭兵破国界始”,进而提出“初设公议政府为大同之始”,最终“立公政府以统各国为大同之中”。当然,我们未必接受康有为的具体制度设计,但他提出的“去国界”“破国界”,或是未来大同的方向。康有为以儒者的口吻指出:“今将欲救生民之惨祸,致太平之乐利,求大同之公益,其必先自破国界去国义始矣,此仁人君子所当日夜焦心敝舌以图之者,除破国界外,更无救民之义矣。”区别于“天下主义”,隶属于“大同主义”的“自由”理念,是一种“可欲的自由”(desirable liberty)。笔者还曾专门讨论过孟子所说的“可欲”问题:“欲”是自由意志的表现;“可”是社会规范的要求。下文将会进一步讨论。
何以“保守”:儒学与保守主义问题
质疑之三:上述既超越古代儒学又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儒家政治哲学,可否称为“自由主义”?抑或某种“保守主义”?对于这种质疑,生活儒学通过揭示儒家的自由传统,进而揭示儒家的“自由保守主义”本质。
前面谈到,有人称生活儒学的儒家政治哲学为“自由主义儒家”,但实际上,更确切地讲,生活儒学的政治哲学并非“自由主义”,而是一种“保守主义”。
(一)“保守主义”概念的澄清
笔者认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异同在于:大陆新儒家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基于对西方“保守主义”的某种认知,这种认知如果不是有意的曲解,就是无意之间的误解。因此,如果要引进“保守主义”这个标签,将其运用于儒家哲学,那么所要保守的传统,决不能是秦汉以降的帝制儒学的政治哲学传统,而只能是孔孟儒学的政治哲学传统。
这就是说,从孔子开始,儒家就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保守主义。当然,孔子的保守主义并非现代保守主义。当时,中国社会正从宗族王权封建的“周制”转向家族皇权专制的“秦制”。孔子称“吾从周”,他所保守的是“周制”,即西周封建制度;他所抵制的则是当时的历史趋势——“秦制”。
不仅如此,孔子的保守主义也可称为“自由保守主义”(liberal conservatism)。近年来,“保守主义”(conservatism)一词常被滥用,往往被泛泛理解为保持“传统”,而不问是怎样的传统。最典型的是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这与“保守主义”这个短语本身的复杂歧义有关。问题的关键在于保守什么,即保守什么样的规范。孔子主张保守的是正义的规范,即正当且适宜的规范,就此而论,可以说孔子是一位保守主义者。本文所说的“保守”,其对象是正义的社会规范,即行为要合乎正当而适宜的“礼”,这是可欲的自由,也是孔子自由观保守性维度的基本内涵。生活儒学的政治哲学,正是这样一种“自由保守主义”。
(二)生活儒学的“自由保守主义”
如果认定孔子的思想是真正的保守主义,那就意味着孔子具有某种“自由”价值观念。不过,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的《中国的自由传统》指出,宋明理学具有“自由传统”。这其实颇有“过度诠释”之嫌。但是,在孔子那里,确实有某种古代的“自由”观念。不仅如此,孔子的“自由”观念甚至具有普遍的意义。笔者从中概括出了一个涵盖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所谓“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的一般“自由”概念:“自由”指个人的意志行为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不受他人干预。
生活儒学的政治哲学所持守的正是孔子思想所蕴涵的这种“自由保守主义”。这个“自由”定义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基本方面。一方面,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孔子指出:“匹夫不可夺志。”这就是说,自由的主体是个人(person),其意志不受他人干预。这既是西语“自由”(freedom)的基本语义,即“免于”(free from ……);也是汉语“自由”的基本语义,即孔子所说的“由己”而不“由人”。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另一方面,个人的意志行为应“在正义的社会规范内”。这又涉及两个层次。(1)自由的前提条件是遵守社会规范(norms),包括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看起来“遵守社会规范”与上述“个人的意志行为不受他人干预”似乎相互矛盾,除非这种社会规范本身就是个人意志的一种体现,即个人要么参与制定,要么同意这种社会规范。(2)遵守社会规范的前提条件是这种社会规范本身是正义的,即这种规范是正当的(公正的、公平的)并且适宜的。假如社会规范本身并不正义,那么遵守社会规范恰恰是不自由的表现。
显然,“正义的社会规范”或“正义的制度”是问题的关键。这也表明:作为一种保守主义的儒学,所要保守的并不是古代的原教旨的“礼”(古代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而是其“仁→义→礼”的原理,尤其是其中的“仁”(博爱精神)与“义”(正义原则)。因为这套原理能够“开出”现代性的乃至超国族的“自由”价值及其制度规范建构。上文已讨论过:这种“正义的制度”并非迄今为止的国族时代的西方自由主义所能提供的。
综上所述,本文回应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家对儒家政治哲学的三点主要质疑,申明了“生活儒学”政治哲学的三点要义:其一,建构“生活儒学”思想体系,以此作为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背景,为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化奠基;其二,建构生活儒学的次级理论“中国正义论”,即情感伦理学的儒家版本“仁爱正义论”,以此超越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形态“国族自由主义”;其三,揭示儒家的自由传统,阐明“生活儒学”的政治哲学本质上是“自由保守主义”。
作者:黄玉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原载:《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6期